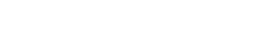编者按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史志工作重要论述和深入学习四史的重要指示,本栏目聚焦“口述校史”系列专题,展陈历代上外人与党同行、与民共进的系列故事,回顾学校自创建以来的光辉历史和办学成就,以此激励所有上外人不忘初心,展望未来。
采访者:何老师您好,您于1960年来上外求学,当初您选择英语专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对语言的兴趣归根到底是对文化感兴趣。当时电台播放俄国作曲家的作品,我又阅读俄国作家的作品,所以一开始主要对俄语感兴趣。但进入大学后选择英语,其一是因为当时感觉英语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其二是对日语、西班牙、阿拉伯语等其他小语种比较陌生,当时上外的相关专业也才开始招生。所以我报考时就将英语列为第一志愿。
采访者:您于1964年毕业后便留校任教,主要教授哪些课程?当时的教学有哪些特点?
当时,学校的青年教师全都住校,白天上完课后,晚上还要监督晚自修,为学生答疑解惑,期间还要加班准备第二天的课程。备课所用的教案由大家轮流撰写,青年教师和老教师共用一本教案,写完后要进行细致讨论。这不仅有利于开展教学活动,更能促进青年教师进步成长。所以我后来做院长时也尽量让留校的老师从精读课开始教授,几年后再根据自己特长教授其它课程。因为精读课的担子最重,覆盖面广泛,对教师要求最高。
采访者:您于1980年赴澳大利亚进修,1982年获教育硕士学位后回国,这段出国深造经历给您带来哪些收获?留下哪些难忘的记忆?
何兆熊:对我来说,这是一段愉快的回忆。因为那时刚逐渐放开出国交流活动,名额还较少。我是第二批赴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进修的,全国高校和国家机关加起来总共8人,上外就我一个。学校并没有给我们提出明确的要求,只是限定了两年的时间。我们听说在悉尼进修的第一批学生已经获得硕士学位,而当时国内鲜有高校设有硕士点。通过了解,那边的硕士学制为18个月,时间上也比较充裕,所以我们就选择攻读硕士学位。这段经历也让我们熟悉了国外的硕士培养模式,澳大利亚作为英联邦国家教学模式接近英国。我们8人分为语言、文学两个方向的学习小组,上课时老师讲授内容不多,从课堂上能学到的内容较少,主要靠学生自学。学校当时派了一个教育学院的老太太负责我们的教学,但也会有其他老师的课程。老师上课时只有一个提纲,与国内的教学模式大相径庭。撰写论文时,导师只让我们自己选择论文题目,甚至也不提供研究方向。这种教学模式给我很大启发,甚至影响了我回国后带学生的模式。因对我们的基本情况不太了解,学校还让我们先上了半年的预备班。由于没有语言学方面的基础,所以当时我攻读硕士学位时还是碰到了一定的困难。但毕竟英语基础比较扎实,加上当时比较肯钻研,我最终还是拿到了硕士学位。
采访者:20世纪80年代初,您为本科生开设语言学课程,80年代中期开始,您还率先在高等院校中为硕士研究生开设语用学课程,当初为什么考虑要开设这两门课程?课程对学生的语言专业能力提升有哪些帮助?
当时语用学在国内的语言研究领域是一个相对新的方向,即便是我在澳大利亚进修的那所学校也没有开设语用学相关课程,不过当时欧洲国家的相关高校是开设这门课程的。我在澳大利亚进修期间阅读了相关书籍,收集了一些资料,回国后便面向研究生开设语用学课程。由于语用学是我的研究方向,从编写教材到备课上课基本是我一个人负责。因为课程内容本身很新颖,学生也非常感兴趣。虽然授课内容比较基础,但给学生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后来我又带几个学生一起把教材升级为英文版,在国内广为使用,对我来说也很有意义。
采访者:1991年12月,您作为富布赖特项目访问学者赴美国俄勒冈大学研修一年,请问这段留学经历和此前的出国深造(澳洲)有哪些不同?
采访者:您从1992年12月至1999年5月先后任上外英语系系主任、英语学院院长(1995年)之职,请问这一期间英语系(学院)的发展有哪些特点?
采访者:您任教四十余年,获得过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高校优秀导师等多项荣誉称号,可谓教书育人的楷模,在您看来,一名优秀的高校外语老师应该具备哪些品质?
采访者:针对新时代外语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您对外语院校的发展及外语人才培养有哪些建议?
何兆熊:现在中学抓得比较紧,学生英语水平提高了,以前的教学大纲已经不太适用。不同层次的院校,应当设定不同的教学目标,好学校可以在语言本身上少下点功夫。有的人觉得精读课已经不重要了,但我个人非常重视英语精读课。学几句英语不难,但学好英语很难,我们生活中还会经常遇到错误的英语用法。我从教多年一直保持上精读课,从院长位置上退下来后,还继续教授精读课。无论培养目标如何变化,打好外语基础依然相当重要。

何兆雄和采访者合影
简介
何兆熊,男,1942年生,广东南海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办公室主任,上海市第十届、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事部全国专业技术职称水平考试专家组成员。1964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现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留校任教。1980年赴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进修,1982年获教育硕士学位。1991年12月作为富布赖特基金访问学者赴美国俄勒冈大学研修一年。1992年12月至1999年5月历任英语系主任、英语学院院长。1988年被评为教授,1994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为博士生导师。
何教授致力于英语语言学研究,重点研究语用学,发表《礼貌和文化价值》《90年代看语用》和《语境的动态研究》等论文二十余篇,专著包括《语用学概要》《新编语用学概要》,主编《语用学文献选读》,参加编写的教材主要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新编英语教程》第5-8册、全国自学考试教材《现代语言学》、21世纪英语专业系列教材《综合教程》第1-4册,选编《<21世纪报>英语读物精粹》1-8册。